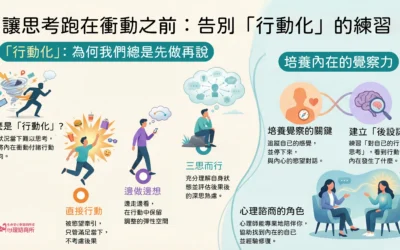「第一次看到,有人比我矮的。」
「我希望妳可以寫下每一個我說的字。」
「今天有事,要請假一次。」
(這可能是第六次的臨時請假)
還有許多、許多,出現在治療室的對話,
有些甚至是第一次見面時,就說出口的。
或許在表達著自己的觀感;
或者是對於心理師理想的期待;
抑或單純地想藉由這樣的方式,
與心理師「建立」連結……
然而,這些對話,
若是發生在一般的社交關係中,
會給對方留下什麼印象?
又或者,倒過來思考,說這句話的人,
想在對方心裡留下什麼感覺?
▊治療的起點
拿上面的例子來思考,當第一次見面的來談者,
直接對著我說:「第一次看到比我矮的。」
此時,這句話所帶來的感覺或效應,
已在彼此的眼中、腦中,乃至心裡,留下些什麼。
這可以是心理師思考與治療的起點,眼前這個人,
正在用什麼方式與他人「建立關係」。

▊心理師的心理空間:涵容
心理師在治療室裡,
思考的每一個點、切入的每一個面,
擴張到對於來談者所呈現面貌的理解,
都會牽動到心理師內在的「心理空間」。
這裡可以連結到,精神分析裡面說的「涵容」。
來個白話文,
就是我們常說,很貼近包容的感覺。
但涵容的意義更為深厚與廣泛,
裡頭有著心理師對於來談者的思考、理解、支撐、
回應、詮釋、調節、修復……等等。

▊表達底下的深意
再延續上例,如果生活裡,
有人第一次見面這樣對你說,你會回對方什麼?
而這個回應裡,有沒有攻擊的成分?
還是保護自己的意味?
或者,
有些人會選擇直接不與這個人接觸(切斷連結)。
而無論是哪一種反應,
都會對應到我們心裡的聲音。
來到治療室裡,
心理師所使用的每一句話、每一個字,
甚至一個眼神的移動,都會讓來談者在說的當下,
與自己有所連結。
舉另外一個例子,
當來談者說著小時候被排擠的經驗時,
心理師在這個時候,挪動了一下位置,
有的來談者可能不會留意,
有的來談者或許會看一眼,也有來談者,
會直接問心理師,這個移動有什麼意思?
這是一個,
直接發生在來談者與心理師的互動之中,
卻也牽動著來談者過往曾經被對待的心裡痕跡。

▊理解這些行為,
是一種希望的表達
當心理師能看到來談者這些表達背後,
那些殞落的心聲、被丟下的無助、被攻擊的憤怒……
才有可能讓深處枯萎的靈魂,得以有光透進的機會。

▊重啟情感連結的能力
當來談者可以與心理師更深進地表達,
這些無法被掀開的記憶、
那些難以被理解的心情、
以及發生在生命裡的種種困難時,
我們才有可能重新在心裡,
長出對人、對環境、乃至對自己的連結。
就像枯萎的靈魂,因著光,得以長出新芽。

▊遇見治療的母親
在治療室裡,很多時候,
光是要和來談者的「某個狀態」進行對話,
大概就可以花上好幾個月。
舉個我之前分享過自身被治療的經驗為例,
我那時候在被治療師戳到心裡的點之後,
開始以各種理由請假~
請假,在精神分析的結構來說,
可以思考為最直接的攻擊: 不去見治療師。
當然,
我會用各種身體不適作為「最合理化」的說詞。
像是,要出門前,肚子開始不舒服~
或是,今天想明天要被分析,
不知道要說些什麼,還是請假好了~
巴拉巴拉~~
然後,當我下一次進到治療室,
就會後悔為什麼上一次要請假。
回到主題,治療師需在這樣持續的來來回回中,
仍然安坐在「那個位置」,
等待來談者可以再次進到治療室裡,說著自己。
無論之前來談者有過多少攻擊、多少破壞、
多少恨意……等等。
慢慢地,來談者可以在這樣的過程中,
經驗到一種「治療師始終在那裡」的感覺。
有如媽媽在看著剛學會走路的孩子,
一掰一掰的起身、邁出第一步,接著呵呵笑著~
或是接下來的嚎啕大哭。
而孩子,可以在時不時的回望當中,
確認媽媽還在那裡。
於是,孩子得以安心地繼續往前探險。
這裡可以連結到
精神分析中的一個觀念:「治療的母親」。

▊長出新的盼望與自己
當來談者可以經驗到,治療關係的連結與深入,
裡頭有著與治療師各種狀態的探索、思考、修復、
長出……等等,
我們便能有一絲盼望:有一天,或者在某個時間點,
來談者可以整合這些在治療室裡的經驗,
內化為心裡的資源與滋養,
長出一個真實且有力量的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