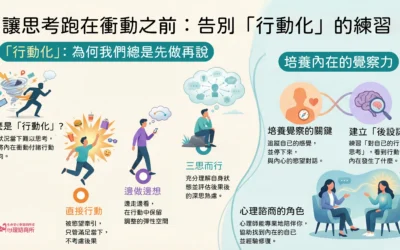台劇《不夠善良的我們》中,
簡慶芬無論是對於何瑞之的執意,或是對何媽媽的由討好到恨意,以及對Rebecca臨終前的照顧,簡慶芬似乎在關係中表露著某一個對待自己的狀態:「對自己的殘忍」。
這份對自己的殘忍,散落在
當何瑞之拿著不合適大小的戒指時,當時的簡慶芬說著:「我可以」
當何媽媽在醫院與簡慶芬說:「回家」
藉由觀察著Rebecca 的生活,來對照自己的生活…
簡慶芬對自己的不夠善良,是當別人把期待或某種樣子丟過來的時候,她會吃下一些擺在眼前的「現實」,然後把自己的奉獻「端出去」,似乎只要「感應」到一絲「可以付出的空間」,那股「奉獻」便無以為繼。
…
在現實生活中,我們也是這樣不夠善良地對待自己嗎?
即便心裡感到不適或感到有所限制,一旦感覺到對方「有需要」的時候,我們便在心裡自動走到了一個「拯救者」的位置,好似整個世界只剩這個足夠善良的自己可以救離對方脫離苦海;然而,這樣的拯救究竟成全了誰?
是我們想把那個無法感到自我認同的自己拯救出框架?
還是我們想把那個煎熬痛苦的自己,藉由對方的脫困,而讓自己感到有所價值?
抑或是我們想把曾經可能加諸在對方的意識,透過實際的行動,變成一個HAPPY ENDING?
到最後,我們想拯救的或是想完整的,究竟是心裡那個痛苦的劇本,還是藉由痛苦成就某一段故事的英雄?